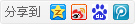為何求知(二)
長沙寬闊的林蔭大道上忙亂紛紛,群情高漲。政治脫離了舊的模式,但還沒有形成新的輪廓。課本被暫時丟到了一邊,學生們不再去寫古文了,而是書寫一些要求美好未來的標語。
一個革命黨的宣傳家來到學校向學生發表演說,承諾要開創一個新時代。毛澤東聽后非常激動,他決定“參加革命”。他花了五天的時間來規劃自己的生涯。之后參加了湖南革命軍(即新軍)。
毛澤東在長沙每月的餉銀是七塊大洋,兩塊用于伙食,其余大部分都用來買報紙。毛澤東看報紙時全神貫注,將其奉為至寶。他買的都是些左翼報紙;媒體是一種信息來源,因為報紙是中國政治生活中一種嶄新的工具。
在《湘漢新聞》上,毛澤東看到曾留學日本的一位湖南人創立了一個“社會主義”黨,其他的文章也大談“社會主義”是一種重新組織社會的新思想。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接觸到“社會主義”這個詞。
那時所謂的社會主義是指帶有集體主義色彩的社會改革,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士兵毛澤東卻深為所動,他熱情洋溢地寫信給以前的同學,向他們介紹社會主義這個頗有吸引力的概念。可是只有一位同學回信。
在政治形勢尚未明朗化的時期,半知識分子總是最有影響的人物。在軍隊,毛澤東開始顯露出自己的半知識分子的特征。毛澤東不愿參加學生組織不只是因為自己年齡大,而且還是因為他對教育一直存在著矛盾心理。
毛澤東擔心學校生活對他的影響。作為毛順生的兒子,他比自己所期望的更像一名有教養的紳士。他喜歡那些沒有文化的士兵把他看作學問人。他后來回顧說:
“我能寫,有些書本知識,他們敬佩我的博學。”他為士兵們寫家信,給他們讀報紙。
雖然其他的士兵都是親自去白沙井挑水,但毛澤東卻是從到營房來賣水的挑夫那里買水。毛澤東朦朧地意識到自己的不明確身份,他回憶說:
“但我是個學生,不能屈尊去挑水,只好向挑水夫去買。”他的父親雖有絕對的權威,但始終未能把澤東培養成為一個地道的農民。
“我以為革命已經過去,”毛澤東在回憶1912年春天時說,“于是脫離軍隊,決定回去念書。”孫中山已和袁世凱達成妥協,袁是個陰險的鐵腕人物,他表面鼓吹共和,內心卻留戀中國過去的帝制。革命的軍事對峙階段已經結束。
毛澤東絲毫也不留戀軍隊生活。在軍隊那段時間,他沒打過仗,只是給長官們辦些雜事。他之所以當兵,是因為他認為軍隊在即將到來的新中國中會起重要作用。他在與一位朋友的交談中激烈抨擊孔孟之道:
“如果民眾都軟弱可欺,那么完善其道德又有何用?最重要的事情是使其強大起來。”
連長和排長們都勸他留下來,但是當他認為軍隊不再是時代的先鋒時,他突然離開了。這位18歲的半知識分子決定重返學校。
去哪所學校呢?毛澤東拿不定主意,于是他查閱《湘漢新聞》和其他報上的招生廣告。學費到哪里去找?家里捎來信說,到現在澤東必須謀份差事了。
這個曾經的士兵住進了很便宜的“湘鄉會館”,開始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流浪生活。
一個警察學堂的招生廣告吸引了毛澤東,但他也喜歡一個開設肥皂制造課程的學校,是因為他認為這對中國的清潔、文明有益嗎?這兩個學校他都報考了,但是即將開學之際,他又退了出來。
他又報考了另外兩所學校,政法學堂和商業中學,他指望這兩個學校對家里會有足夠的吸引力,能從他父親那兒弄到學費。毛澤東在第一次談到他給父親寫信要錢時說:
“我向他們描繪了我未來的美好前程,我說我會當律師或做大官。”還沒等到家里回信。這位猶豫不決的青年對這兩個學校又失去了興趣,當然也又一次搭上了報名費。
毛澤東不斷地接受同學的勸告,今天聽這個的,明天又聽那個的。但是他什么也沒有決定下來。他什么都想抓住,結果一無所獲。
不久,毛澤東瞄準了一個目標,他花錢報考了一所高級商業學校。毛順生同意支付學費,“我父親是很容易理解善于經商的好處的”,年輕的毛澤東坐下來學習經濟。
他起初肯定不知道這所學校的很多課程和教材都是英文的。他的英文并不好,只是在東山高小時學了點入門的知識。
毛澤東回憶說:
“這種情況使我不滿,到了月底,我就退學了,并且繼續留心報上的廣告。”
不名一文,邋里邋遢,毛澤東無所事事地混跡于長沙街邊的木茶棚里,用他那發呆的大眼睛盯著報紙。干什么去呢?
毛澤東一度以嘲弄的態度對待周圍的生活。他看到了一切事物的兩重性,他反求諸自身(其思維我們無從得知)。他坐在人生的高處,俯視忙忙碌碌的蕓蕓眾生。
“我即宇宙!”他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結論。
湖南省政府軍的軍火庫爆炸,烈焰熊熊,他和朋友們一道去觀賞。一年前他曾滿懷激情地參加了這支軍隊。但是現在,他以旁觀者取樂的口吻說:“這比放爆竹要好看得多了。”
一天,三個學友在天心閣的頂樓上碰見了毛澤東,他正獨自專注而平靜地在城墻的這個七層高塔上俯瞰長沙。毛澤東從冥思中回到了現實,四人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這三個青年在社會地位上都比毛澤東高一等,其中一個常常借錢給他。對于政治,從世故的角度來說他們比他更懂。一位姓譚的青年是大官的兒子,他說君主制的廢除就意味著“我們都可能當總統”。
當另一個學友說一些俏皮話來揶揄譚時,毛澤東不再悶聲不語了,他激動地說:
“讓他說,我很感興趣,讓他說吧!”譚繼續解釋。對一個政治領袖來說,學問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爭意志。毛澤東被這種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他深思著,就像凝視長沙的紅屋頂時那樣。
表面上看來優柔寡斷的這個流浪者,實際上似乎正在孕育著一種新的世界觀。
他又踏進了另一所學校的大門——湖南省立第一中學,但6個月之后就離開了。他對考學已很自信,在報考第一中學的考生中,他名列前茅。也許有些自鳴得意,毛澤東對學校作了兩點批評:
“它的課程有限。校規也令人生厭。”㈤這很能說明年輕的毛澤東的性格特征。
一位教員借給毛澤東一本很有趣的官方史書——《御批通鑒輯覽》。這本書為他下一步的行動提供了跳板。和課堂上講的東西相比,他更喜歡這些諭旨、法令以及皇帝的御批等等。于是他決定自學一段時間。
好像6個月是毛澤東興趣轉移的自然跨度,他整天泡在湖南省立圖書館的時間也是半年。
他總是早上開館就進去,下午閉館才出來。他一動不動地坐在書桌旁埋頭苦讀,好像一尊低著頭的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只是中午出去買個燒餅或幾個包子當午飯。
他飽覽了現代西方的歷史和地理。為了擴大知識面,他又轉涉小說、中國詩詞和希臘神話,還有改良派嚴復新近翻譯的亞當,斯密、斯賓塞、穆勒和達爾文的名著以及盧梭和孟德斯鳩的作品,毛澤東在《世界英雄豪杰傳》中就熟悉了后兩位思想家。
他凝視著掛在圖書館墻壁上的《世界堪輿圖》。他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地圖:中國只是一個國家,與其他幾十個國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邊境線把中國與外國分開,中國在這上面不是一個“中央帝國”。
他笑著對愛彌·蕭說,在省立圖書館,他就“像牛闖進了菜園子”。他后來認為,這半年的書海生涯對他的生活影響很大。
在不得不和別人共事時,毛澤東表現出一些猴氣;但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時,他又會很有虎氣。
毛澤東每晚都回到“湘鄉會館”,這里住滿了當過兵的人、學生、過路客和一些虛度時光的閑蕩漢。
有天晚上,這里發生了一場武斗,士兵們襲擊并想殺死學生。毛澤東此時似乎仍帶著點道家自我保護的思想,而不像一位挺身而出的公民。他回憶那個血腥的夜晚時說:
“我躲到廁所里去,直到毆斗結束以后才出來。”
房租是不能用讀書的熱情來交付的。不久,經濟上的拮據迫使毛澤東又去查閱廣告欄。他偶然發現了教書,一所師范學校的
廣告吸引了他:免交學費,食宿便宜,畢業后會成為一名教師。
毛澤東的兩個朋友也力勸他進這個學校,他們指望毛澤東在入學考試時幫助他們,毛澤東答應了,便寫了三篇文章。
“當時我并不覺得自己替朋友寫文章的行為是不道德的。”他回憶說。他認為這皂友誼,他很高興顯示一下自己的文學才能,就像在軍隊時那樣。
三篇文章使他們都考進了這所學校。家里同意了毛澤東的選擇并給他寄來了錢,聽憑興趣、率意而為的時代已經結束。在23年后毛澤東回想起當年這段漂泊無定的生活,不禁有些好笑,他說:“從此抵制了所有吹噓未來前途的廣告的引誘。”
政局變得更糟,袁世凱喪心病狂,企圖恢復君主制,并要登基當皇帝。在這個銀樣鍛槍頭的新復古派和孫中山領導的立場動搖而又松散的激進派聯盟間互相角力造成的緊張氣氛中,軍閥們悄悄登場了。在長沙,一名軍閥謀殺了兩位在1911年起義次日上臺的激進派領袖。到1917年夏,中國出現了兩個政府:一個是北京的軍閥政府,一個是孫中山領導的廣州政府。
日本在蠶食中國,但是沒有人出來組織全國性的反抗。軍閥亂于國內,列強迫于門外,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痛苦——湖南的生豬產量十年內下降了一半——在知識分子中間也出現了悲觀絕望的想法。

中國雖已脫去舊的外殼,但是還沒有獲得新生。
這一切現象對毛澤東來說不是壞事。他還是需要冷眼旁觀思索,而不是要去做些什么。這是接受良好教育的大好機會,他抓住了這個機會。一段早年的課堂筆記道出了他學習的樂趣:
“有了什么念頭就隨時記下來,頭腦里有什么想法就高興地表達出來,有助于保持平衡。”
毛澤東和其他400名身穿藍色毛紡制服的學生一道人了學。學校兩層樓的圓柱、拱頂和庭院完全仿照英國殖民地建筑的風格(其實是日本式的建筑翻版)。
和中國的一切高等學府一樣,第一師范也是一所新學校,但它的設備和條件都不錯,而且優秀的教員們繼承了湖南的學術傳統。
第一師范的外墻上寫著校訓:
“實事求是”,所謂的“事”和這里的建筑一樣是中西兼顧的。毛澤東上午讀中國歷史,午休時間看德國哲學。
毛澤東仍然精瘦,更顯出一雙大眼睛炯炯有神。他的發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一件灰色長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談舉止還是慢條斯理,他不是那種講起話來滔滔不絕、指手畫腳的學生,在聚會時更是很少說話。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求學時的毛澤東
通過許多課程的學習。毛澤東選擇了自己的路。他閱讀了亞里士多德、霍布斯、邊沁、柏拉圖、康德、尼采和歌德的部分著作。他在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Princip1esofSociology)中遇到了一個觀點,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是這樣解釋的:“一則美國的格言說‘吾國說對即對,吾國說錯即錯’。”他有著廣泛的好奇心并對折中主義有很高的興致。他在給蕭瑜的一封信中說:
“耶穌被斷章取義了,這樣做的人未必有罪,即便真的有罪于一個睿智的人來說也不足掛齒。”
毛澤東說:
“這所新學校有許多規則,我只贊成其中的極少數。”在第一師范,他既有足以稱道之事也有有失顏面的事。一次他讀書到深夜,被子靠油燈太近,引起了一場小火災,燒壞了幾張床鋪。還有一次,一位同學因父母包辦婚姻而苦惱,毛澤東深表同情,到這位同學家,勸說他的父母放棄他們的安排。
在第一師范,人們很少呼他的名——澤東,而是叫他的字:潤之,其意思是“施惠”或“潤澤”。
毛澤東對于不喜歡的課程,如靜物寫生和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連碰都不碰,經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對他喜歡的課程,如撰寫文學或倫理主題的文章和社會科學課程,他學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獨到見解,常得100分。
完全放棄枯燥的靜物寫生課不是毛澤東的做事風格,他不得不硬著頭皮應付一下。在繪畫考試時,他在試卷上潦草地畫了個橢圓,題名“雞蛋”,然后就離開了教室。一天上課時,一個簡潔的構思使他得以提前離開教室。他畫了一條水平線,在上邊又畫了個半圓,題名“半壁見海日”
(這是唐代李太白的一句名詩)。他的繪畫成績不及格。
毛澤東仿照維新派風云人物梁啟超的自由文風寫出了熱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國文教員袁大胡子,“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
袁還說毛澤東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后都標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將他寫有日期的那一頁文章撕掉了。毛澤東站起來,抓住袁的胳膊,問他到底想干什么,要拉他到校長辦公室去“評理”。
奇怪的是,這個對很多管束都進行反抗的青年卻接受了古典文風對他的塑造。
“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他有點不坦率地說。實際上,他在心理上還是傾向于古文形式的,特別喜歡無神論學者韓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后,毛澤東對埃德加·斯諾說:“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
(“如果需要”,這句話含有諷刺意味,因為,毛澤東這時已開始對其他人用古文寫成的文章大張撻伐了。)
因此,當毛澤東在政治上比改良派還激進時,他的文學風格還是落后的。他在文風崇古和政治革命兩方面雙雙背離梁啟超。
他開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在1919年給蕭瑜的信中他寫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個人只有身患惡疾時才知道健康的幸福”。
毛澤東在第一師范所受的教益主要來自道德哲學和報紙——這是他持續終生的兩個愛好。
和絕大多數青年一樣,毛澤東也從他的榜樣和道德訓誡那里學到了一樣多的東西。從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門徒的人物,這位具有過激精神的紳士因為提倡寡婦再嫁而震動了整個長沙。這就是楊昌濟,他是一根往舊中國的軀體中輸入新鮮血液的導管。

楊昌濟的生活方式是傳統的——人們稱他“老夫子”。他講課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義的一代人的心靈中播下了會結出激進果實的種子。
楊昌濟尊崇宋明理學(始于10世紀),但也花了四年的時間在英國和德國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歐洲思想家的理論。使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是他對心靈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于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無疑,這是個人主義,但這是著眼于整個社會進步的個人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