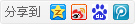毛澤東身後的國際影響力:曾改變了一代西方人
當新世紀第六個“9·9”——2006年9月9日來臨之際,我們再次想起了整整30年前,一顆巨星的隕落——一代偉人毛澤東與世長辭。這位偉人對中國的意義不言而喻,當年也曾在全世界範圍內引發了巨大的“毛澤東熱”。30年後,毛澤東的影響力在世界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毛澤東影響一代法國人
在歐洲,法國人對毛澤東的瞭解也許是最多的。從市井小民到名人政要,知道毛澤東的法國人,就像知道拿破崙的中國人一樣普遍。
記者時常與法國人聊起毛澤東。隨便跟他們提起這位偉人,他們都能聊上兩句,而且通常都很準確。法國電視二臺每週都有一個《大家都這麼講》的對話節目。一次,中國變性舞蹈家金鑫應邀來做節目。那天,金鑫穿了一身軍服似的套裝。主持人打趣說:“毛澤東的時代都過去那麼久了,您怎麼還穿軍裝?”金鑫聰明地答道:“看好了,這可是香奈爾!”主持人哈哈大笑——他明白,金鑫是在說:法國人抄襲了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時髦。
一位主持人竟能隨口冒出“毛澤東的時代”,可見法國人對毛澤東瞭解之深。
一些在法華人調侃說,法國有一群毛澤東的“專業粉絲”。這群人數量很大,且幾乎個個是名人。這些“專業粉絲”是怎樣形成的呢?1968年,法國發生“五月風暴”。“風暴”從巴黎大學開始,大批學生集會抗議反越戰學生遭逮捕。抗議活動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大,不久後,全法學生都加入其中,上千萬工人也行動起來。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就是當年的一名抗議學生。如今,他仍是毛澤東的崇拜者。他說:“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對法國青年簡直是種‘誘惑’,它激起了法國青年的反叛精神和改變世界的願望。”與他一樣,“很多青年都崇拜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敢於同強權作鬥爭,不屈服於外部壓力。毛澤東的這種精神,成為當年抗議活動的重要動力之一。
當年的那批青年學生,如今有很多都成了法國社會的名流,比如: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貝爾納·德博爾,《解放報》剛剛離任的總編塞爾日·朱利,2007年大選熱門人物之一霍郎德·卡斯托,心理學家熱拉爾·米勒,左派無產階級組織領袖阿蘭·熱斯馬爾……數不勝數。
法國國際問題專家稱,毛澤東影響了整整一代法國人。也有人說,毛澤東的影響不限於一代法國人,因為當年的那批青年人,如今早已為人父母,他們會將自己對毛澤東的情結,在言傳身教中傳給子女。
西方藝術界“活著的大師”:我是“毛派藝術家”
約爾格·伊門道夫是德國著名的畫家和雕塑家,被西方藝術界稱為“活著的大師”。而伊門道夫本人則以“毛派藝術家”自居,他始終崇拜中國偉人毛澤東。
為毛澤東逝世而流淚
第一次見到伊門道夫,是5年前在柏林的一次聚會上。他當時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褲,戴著金表、金戒指和金項鏈——這是他的招牌裝束。不過,引起我注意的卻是他左臂上刺著的“毛”字。
伊門道夫與我的第一次談話自始至終沒離開毛澤東。“矛盾論”、“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個個熟悉的名詞從他口中接連“蹦”出。“年輕時,我讀過很多毛澤東的著作,比如《矛盾論》、《實踐論》等。”他說。
交談中,伊門道夫告訴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大批青年學生因對蘇聯印象不佳,轉而關注中國。正在杜塞爾多夫讀書的伊門道夫和許多青年一樣,深受毛澤東的影響。“當時我就覺得,毛澤東思想非常革命。”他參加了一個名叫“團結”的組織,之後開始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
伊門道夫說,他最難忘的日子是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的那一天。當他通過各種管道確認這一噩耗的準確性後,悲痛欲絕地流下了眼淚。第二天,他忍住悲痛,在就讀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組織了一個悼念儀式。
伊門道夫告訴我,他有幾間房子專門存放毛澤東紀念品,足有幾萬件,僅《毛澤東選集》就有20多個版本。
在毛主席遺體前,自己很渺小
在兩年前伊門道夫舉辦的一次畫展上,我再次見到了他。
20世紀60年代,伊門道夫一度打算放棄繪畫,尋找一種能抵制資本主義美學的藝術形式。然而,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使他重新回到了繪畫道路上。
《咖啡館德國》是伊門道夫在這次畫展中推出的得意之作,畫面處處透出對國家命運和社會的深層關懷。伊門道夫對我說:“你看看這幅作品,就是這幅,裏面滿載著我對毛澤東的尊敬。”
伊門道夫坦言,他年輕時就是一個左派甚至是“毛派”,如今他的思想更接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974年,他提出了“藝術屬於人民”的觀點。這個觀點來源於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德國評論家們給他扣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畫家”等名號。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世界收藏界卻由此掀起了一股“伊門道夫風”。如今,他每幅作品的起價都在50萬歐元以上。
20年前,伊門道夫帶著他的作品,第一次來到了他心目中的“聖土”——中國。一下飛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到毛主席紀念堂,虔誠地在毛澤東遺體前停留良久,出門時還買了3冊毛主席紀念堂珍藏書畫冊。他說:“在毛主席遺體前,我覺得自己很渺小。有機會參觀毛主席紀念堂是我莫大的榮幸。”
毛澤東思想支撐著他
1個月前的一天,在德國一所藝術學院裏,我第三次見到伊門道夫。據說,前一天,他的家剛被小偷光顧過,損失了百萬資財。不過,他的心情好像沒有受到影響,笑聲依舊爽朗,常常是我問一個問題,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一生都“招供”了。他告訴我,毛澤東思想對於他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情結,這也是他從1993年開始就持續不斷地到中國辦畫展的原因。難怪有評論家說,像伊門道夫這樣一個世界級的大師,在一個第三世界國家頻繁辦展覽,“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伊門道夫還嚴肅地和我談起了他對毛澤東的總體評價:“毫無疑問,毛澤東是20世紀世界上最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他認為,毛澤東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他在五大洲都有擁護者,就是最好的證明。”人們對當今中國的興趣越來越大,自然會去研究毛澤東,因為大家都想知道:毛澤東對20世紀的中國到底有多大影響?
很快到了用餐時間。這時我才發現,伊門道夫的手顫抖得很厲害,連夾菜都要助理幫忙。他的學生告訴我,因為身患重疾,伊門道夫連穿衣、點煙、吃藥都需要人照料,更別說是作畫了。
伊門道夫的身邊,有一位年輕甜美的女士一直寸步不離。那就是他的妻子。她告訴我:“你看到了,他的身體不如以前好,但支撐他身體的力量仍然很強大,那就是他的思想。”相信在他的思想中,毛澤東思想占著很重要的分量。
兩次重走長征路的英國人菲力普·肖特:毛澤東把我帶到中國
低矮的房屋,青石鋪就的樓板,牆壁殘留著的革命年代的口號,還有老年人唱著的紅軍時代的歌謠……這一切都讓一個外國人如癡如醉。20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十億人民九億商”的時候,一個英國人卻執著地來到中國西北,追尋一位偉人的足跡。6年中,他兩次重走紅軍長征路,遍訪韶山、吉安、瑞金、遵義、延安等地。這位英國人就是英國廣播公司(BBC)駐中國記者站首任站長菲力普·肖特,而他追尋的那位偉人,就是毛澤東。
娶中國妻,走長征路
肖特的祖父曾在19世紀末的香港當過海關檢查員;20世紀30年代,他的叔叔曾作為船長到過廣東、福建。因此,早在學生時代,中國這個東方的古老國度,便對肖特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1966年夏,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肖特,向中國駐英國代辦處提出了去北京當教師的申請。可惜,那時中國剛剛爆發“文化大革命”,他的申請未能得到批準。然而,毛澤東揮手之間的睿智和光芒卻已經在這個21歲的英國人心中紮下了根。11年後的1977年,肖特被選做BBC駐北京記者站的首任站長派到中國,而且一幹就是4年。他終於可以近距離感受“做夢都會想到”的毛主席了。
因為對毛澤東的著迷,肖特娶了一位中國姑娘為妻,並在他年近50歲的時候做了一個決定:重走長征路。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不少地方仍然貧困。在一個冬天,天空飄著雪花,肖特和妻子住進了西北某地一家很小的旅店。房間外時常有小孩子好奇地探著頭,瞧著這位古怪的外國人。當地的黨委書記告訴肖特,他是自1934年以來,第一個到訪這裏的外國人。肖特回憶那6年間的“追夢之旅”時,感慨地說:“條件很艱苦!可想而知,當年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是如何從這裏走向北京的。”
7年寫就《毛澤東傳》
6年長征路,肖特收穫的是滿滿10大箱檔和資料。他採訪了許多與毛澤東交往過的當事人。儘管不懂中文,但他仍然從毛澤東遒勁的書法中看到了什麼——“毛和他的詩與書法作品一樣,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精神”。肖特想進一步探究這種精神,因此,在1981年離開中國後,他仍然每年都回來,參觀毛主席紀念堂,瞻仰天安門城樓上的那張巨幅偉人照片。
“我一生都被中國所吸引,而對毛澤東,我一直很崇拜,他是20世紀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政治家之一。”說這話時,虔誠的肖特顯得很開心,除了因為談的是毛澤東,還因為他每次回來都能看到這裏的巨大變化。
終於,肖特在從事記者生涯25年後,歷時7年寫成了《毛澤東傳》這本70萬字的“巨著”。有意思的是,他將這本書設計成“紅寶書”的模樣——紅封面紅封口,通體通紅。寫完《毛澤東傳》,肖特回到中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天安門城樓下,以一個標準的中式姿勢,將紅彤彤的書抱在胸前,“瘋了似地拍照”。
“當寫完最後一個字時,我感到了一種徹底的解脫,但同時也有深深的失落感——我好像是離開了我的母親,變成了一個孤兒。”肖特認為,這不僅意味著實現夢想、登上峰頂的興奮,更意味著他已經從深厚的毛澤東情結和人生經歷中分娩出一個新的自我。
數十年的毛澤東情結、6年長征路、10箱有關毛澤東的資料,使肖特決定為自己的孩子留下中國國籍,以延續他與毛澤東和毛澤東建立的這個國家最直接、最緊密的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