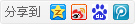京沪天地(二)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200 万人)已成为西方的门户,商业贸易是其血脉。毛泽东不喜欢待在上海,因为这里没有古迹、胜景和名山吸引他。
他丢拜见通过《新青年》结识的他的第二个楷模陈独秀教授,这位研究文学的学者1917年迫于军阀的压力从北京搬到了上海。这次会面为日后的进一步接触播下了种子,尽管这个第一次会面还没有到火候。

毛泽东在上海漫步街头,阅读报纸,拜访湖南友人。他浩渺的心思回到了在长沙的事务上。有一桩好事来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拨给他一笔钱,使他得以回湖南。1919 年 4 月,毛泽东打起行囊,步行兼乘车船回到了长沙。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当时毛泽东的境况非常艰难。他在湖南大学为投考者而设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不久,他在母校第一师范的附属小学兼些历史课的教学。毛泽东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确实没法从事固定的工作。
毛泽东过着清贫的物质生活,尽管他的思想漫游在常人所不及的世界里。他一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草鞋便宜而且在夏天更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日常生活中,他经常要依赖别人。
北国之行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在北京时他沉默寡言,在长沙他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第一次冒险举动是公开地讲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奇思想,虽然对此他只知一点,也只这么一点。
1919年下半年,毛泽东成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两个主题。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湖南军阀统治者张敬尧,这位半封建式的亲日派曾使五四学生付出了血的代价。
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使运动主旨的两个方面都做得出色。在骄阳似火的6月,他在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学生运动的热情空前高涨,这在全国首屈一指,即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骚乱较之也略逊一筹。学校有半数时间停课(理想的“真理”压倒了现实)。一纸宣言可以引起学生第二天更大规模的游行。包里装着牙膏,背上用毛巾袋裹着雨伞,学生们走出长沙与其他地方的志同道合者取得联系。几乎每个人与自己的家庭都发生冲突。印刷粗糙的小型杂志不断涌现,标题都带着一股高昂的情绪:
《觉悟》、《女界钟》、《新文化》、《热潮》、《向上》、《奋争》、《新声》 。
以20世纪60年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学生绝不摩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身穿长袍马褂的绅士,惯于对仆人指手画脚。他们一只脚站在传统的门槛里面,嘴上却言辞激烈地反对传统。与美国的一些福音派信徒一样,他们和周围人一样生活,但嘴上却说是周围的人污染了他们纯洁的心灵。
有一个大学生剁掉自己的两个手指以抗议督军张敬尧的残暴行径。13岁的丁玲(她后来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带领全班同学冲进湖南省议会的议事厅,要求妇女有财产继承的权利。年龄越小,他们越无所顾忌。
毛泽东在一个“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集会上发表演讲,而没有注意到中国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事实。他组织一批女学生——从一开始他就把女学生吸收进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核心——在长沙街头检查店铺,警告老板要销毁日货。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当时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事实的确如此,晚间政治活动之后一两个小时的休息,不带邪念的男女相依而卧不会发生情事。毛泽东和“三杰”之一的蔡和森及他聪明美丽的妹妹蔡畅曾立下三人盟约:发誓永不结婚。但是他们三人都违背了这一誓言,毛泽东则违背了三次。
这不表明他们的誓言是戏言,而是表明他们一度曾经具有的思想——像美国福音信徒——他们并不羞于生活在矛盾中。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但爱情悄然而入,而且常常为他们的事业增添光彩。
学生的社会处境使他们处于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是蒙耻受辱的一代。古老传统的粉碎使他们根基顿失,国家的风雨飘摇又使他们濒临绝望。
做旧中国的反叛者要求具有很大的胆量来付诸行动。对外表堂皇、内部腐败的旧中国的公然反叛,犹如挥戈猛刺一个外皮尚好、里面烂如狗屎的西瓜,民众会哄然大笑。咒符既被揭破,烂透的西瓜又始发青春。在1919年的中国唤起民众的反抗并非难事。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毛泽东为学生联合会而奔走忙碌,他创办了一份周刊,自任编辑和主笔,并依地名将该刊物命名为《湘江评论》。第一期《湘江评论》印了2000份,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以后每期印5000份 (这在1919年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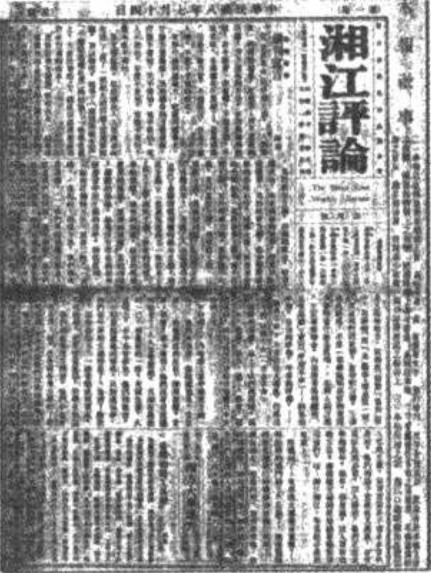
该杂志锋芒犀利,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主旨。它使用白话文而不是呆板的文言文,语言的改宗就如用耶稣的原话改写钦译圣经一般的惊人。
的确,甚至胡适教授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他在红格薄纸上草就的文章笔锋锐利。生动活泼,对每一个论点都表述得很详细。他以前如饥似渴地读报纸终见成效。
“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毛泽东作为编者在发刊词中宣称。“什么不要怕?”他作出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当时超然的思想:“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在中国的一份报纸上,我们看到当时的一位小学教师对毛泽东的回忆,文中不乏溢美之辞,但很有史料价值。
《湘江评论》只编写5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着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
毛泽东写的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集中表达了他的观点。这篇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极富爱国热情,尽管还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与两年前的《体育之研究》有明显的不同。毛泽东开首便直刺中国社会现状:“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他不再认为强健个人体魄是解救中国之关键。中国确需这样一种修道士——毛泽东是他们中间的头一个——来带领中国走出黑暗。不过,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并没有提出领导权。
他尽可能争取广泛的支持,号召各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势力“齐声一呼”。这联合将半靠自觉半靠组织,巩固的团结是其关键。1911年辛亥革命未能发动民众,下一次革命非唤起民众不可。
文章提及了马克思(“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以与毛泽东欣赏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生在俄国的, 叫做克鲁泡特金” )相比较。毛泽东说,马克思的观点“很激烈”,克鲁泡特金更温和的观点虽不能立见成效,但是他的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人手”。
文章富有革命色彩,但是在1919年的长沙,马克思与其他一些革命理论家相比,似乎并不引人注目。毛泽东期望一种更为公平的社会秩序。他有出色的组织才能,但是当时的毛泽东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形态。
毛泽东设想多种形式的联合会汇聚力量形成革命大潮。联合的目的很简明:“反对压迫民众的……强权者”,妇女、人力车夫、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都包括在这种联合之内,没有阶级界限之分。
毛泽东以设身处地的口吻述说了各阶层的苦难,而对学生之苦则最为激动:
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 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谈西方事务的文章笔力雄健,但有时也很怪异。他认为德国的“唯一出路”是与俄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成一个“共产共和国”。巴黎和会后,他讽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说:“无知的克里孟梭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暗指巴黎和约),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样的稳固。”另外,黄雨川在《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中说,毛泽东当时并非像李锐所说。单独负责《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
在学校时,毛泽东就造过现已与之不存在联系的老师的反。现在,他要造社会的反。他信誓旦旦:
“我们倘能齐声一呼, 必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
毛泽东的文章受到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的赞扬(“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这激励了长沙合作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在艰难中形成。
在开始公开自己的观点中,毛泽东转入一新的开端。读书学习,在书页上写一万字的批注是一回事,在公众面前亮相则是另一回事。这是一种行动,其言论将会造成后果。毛泽东不再只是探索周围的世界,而是在逐步改造这个世界。
军阀张敬尧查封左派刊物的习性,就像看门人在能源危机时熄灭灯火一样。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一夜之间就把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扼杀了,它的主办者湖南学生联合会也在同一夜被取缔。
当时各种小型杂志多如飞雀,过眼即逝。毛泽东很快又入主《新湖南》杂志,这家由湘雅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主办的杂志同样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因暑期人手短缺,故欢迎毛泽东去当编辑。该杂志创刊于6月,8月份由毛泽东接管,10月份便遭到了与《湘江评论》同样的厄运。但是它被查封之前引起国内左派的更多注意。
毛泽东的文章被长沙的主要报纸《大公报》采用,他作为政论家已享有一席之地。忽然间,当地发生了一起可以大做文章的新鲜事。
长沙有位赵女士准备出嫁,她不喜欢择她为妻的那个男人,但是四位老人——她的父亲是眼镜制造商、男方的父亲开古董商店——都极力促成这桩亲事。娶亲的那一天,赵女士穿上新娘的服装上了花轿。在往新郎家中的路上,她突然从裙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割破喉咙自杀了。
悲剧发生不到两天,毛泽东写的《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就见报了。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内,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八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文章。
如往常一样,毛泽东从自己的生活中挖掘社会罪恶的根源。
他谴责社会:“赵女士的自杀,完全是环境所决定。”毛泽东言辞掷地有声,“这种环境包括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思想不能独立,爱情的不能自由。 ”他把赵女士结婚的花轿称作“囚笼槛车”。
从这九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的包办的婚姻对他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逆来顺受。“大男子主义”已被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
毛泽东以父亲般的口吻写下《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在另一篇文章中, 他呼吁读者 “振臂一呼”,砸碎迷信的枷锁。勇往直前早已是他的一条信念。
“命定婚姻,大家都认作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 ”
自此时起,毛泽东终生都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自杀的思想。“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像赵女士那样自杀不是对腐朽的旧社会的反抗,它实际上迎合并维护了即将灭亡的旧道德秩序。毛泽东写道:“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毛泽东鞭挞了妇女贞节牌坊,这在当时给人印象极深:“你在哪里看见男子贞节牌坊吗?”这个几乎可以肯定还是童身的男子问道。接下来,他召集女学生走上街头说服家庭主妇抵制日货,争取各方支持反对军阀张敬尧的罢工。
毛泽东的思绪被新民学会的名称牵回。妇女运动只是造就新民的开端。不过毛泽东正在逐渐接近这样一个观念,即建立帮苹会应该是最终的目标。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与张敬尧的湖南政权处于冲突之中,至1919年12月引来了镇压。张敬尧的军队用刺刀和枪托驱赶在教育广场焚烧日货的人群。深夜召开的筹划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毛泽东写了一篇呼吁推翻亲日派军阀屠夫张敬尧的宣言。
13000名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宣言上签了字,长沙大罢工开始了,胜负要见分晓了。张敬尧没有被推翻——尽管他的统治动摇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头的人大祸临头。
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以逃避张敬尧的追捕——张敬尧现在对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他要到湖南以外的反军阀势力那里去寻求对驱张运动的支持。毛泽东重返北京。在北京的四个月是他收获的季节,尽管并不尽如人意。
毛泽东是由新民学会派遣北上的。他是由100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的团长。毛泽东还接受了《大公报》和其他报刊的任务,他这次不再是身无分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