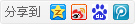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
三月間,我在這個地方同黨內的一些干部講過一次話。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一百天了。這一百天,時局有很大的變化。我們同資產階級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覺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當大的提高。當時我們就料到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這里說過,人家批評起來,就是說火一燒起來,豈不是疼嗎?要硬著頭皮頂住。人這個地方叫頭,頭有一張皮,叫頭皮。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著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得對的就接受,說得不對的加以批評。
我們總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們中國也好,多數人是好人。所謂多數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國六億人口中,工人、農民是我們的基本群眾。共產黨里,青年團里,民主黨派里,學生和知識分子里,多數人總是好人。他們的心總是善良的,是誠實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別有用心的。應當承認這一點。這是每一次運動都證明了的。比如這一次,拿學生來說,北京大學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堅決的骨干分子,經常鬧的,鬧得天翻地覆的,始終只有五十幾個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為他們拍掌的,擁護他們的。
放火燒身可不容易。現在聽說你們這個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沒有放得厲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點不夠,有點不過痛,早知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讓那些毒草長嘛,讓那些牛鬼蛇神出臺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個時候我就講不要怕。我們黨里頭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亂。我說,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為黨為國,就是沒有看見大局面,就是沒有估計到大多數人,即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眾,他們是跟我們一塊的。他們可以罵我們,但是他們不用拳頭打我們。右派只有極少數,象剛才講的北京大學,只有百分之一、二、三。這是講學生。講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這兩方面旗鼓相當。中間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們有些同志, 就有那么一些怕, 又怕房子塌下來,又怕天塌下來。從古以來,只有“杞人憂天”[1],就是那個河南人怕天塌下來。除了他以外,從來就沒有人怕天塌下來的。至于房子,我看這個房子不會塌下來,剛剛砌了不好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來呢?
總而言之,無論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是我們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眾呢?怕群眾是沒有道理的。什么叫領導人物呢?小組長、班長、支部書記、學校里頭的校長、黨委書記,都是領導人物,還有柯慶施同志,我也算一個。我們這些人總是有那么一點政治資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點事。現在把火放起來燒,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們的同志燒好。我們每一個同志,都有一點毛病,那有沒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總要講錯一點話,辦錯一點事,就是什么官僚主義之類。這些東西往往是不自覺的。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們覺得以后是一年燒一次,還是三年燒一次?我看至少是象閏年、閏月一樣,三年一闖,五年再闖,一個五年計劃里頭至少搞兩次。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頭一鍛煉就更好了。孫悟空不是很厲害的人物嗎?人家說是“齊天大圣”呀,還要在八卦爐里頭燒一燒。不是講鍛煉嗎?鍛者就是錘打,煉就是在高爐里頭煉鐵,平爐里頭煉鋼。鋼煉出來要鍛。現在鍛要拿汽錘鍛。那個鍛可厲害哩!我們人也要鍛煉。有些同志,你問他贊成不贊成鍛煉,那他是很贊成的,“啊,我有缺點,很想去鍛煉一下”。人人都說要鍛煉一番。平常講鍛煉,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鍛煉了,真正要拿汽錘給他一鍛,他就不干了,嚇倒了。這一回就是一次鍛煉。一個時期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就是兩股風來吹:一是大多數好人,他們貼大字報,講共產黨有缺點,要改;另外是極少數右派,他們是攻擊我們的。兩方面進攻的是一個方向。但是多數人的進攻是應當的,攻得對。這對我們是一種鍛煉。右派的進攻,對我們也是一種鍛煉。真正講鍛煉,這一回還是要感謝右派。對我們黨,對廣大群眾,對工人階級、農民、青年學生以及民主黨派,右派給的教育最大。每一個城市都有一些右派,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們的。對這些右派,現在我們正在圍剿。
我們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六億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業。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的事業,社會主義建設是人民的事業。那末,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好不好?有沒有成績?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業的成績。這是第一條。第二條,走那一個方向呢?走這邊就是社會主義,走那邊就是資本主義。右派就是要倒轉這個方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三條,要搞社會主義,誰人來領導?是無產階級領導,還是資產階級領導?是共產黨領導,還是那些資產階級右派來領導?右派說不要共產黨領導。我看這一回是一次大辯論,就是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大辯論。辯論一次好。這些問題沒有辯論過。
民主革命是經過長期辯論的。從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凱、北伐戰爭、抗日戰爭,都是經過辯論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論,說中國的槍不夠,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說不怕,還是人為主,武器不如人,還是可以打。后頭接著來的解放戰爭,也是經過辯論的。重慶的談判,重慶的舊政協,南京的談判,都是辯論。蔣介石對我們的意見,對人民的意見,一概都不聽,他要打仗。打的結果,他打輸了。所以,那一場民主革命是經過辯論的,經過長時期精神準備的。
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內,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小生產者個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雖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還差。社會主義改造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單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層建筑,主要是政權機關、意識形態。比如報紙,這是屬于意識形態范圍的。有人說,報紙沒有階級性,報紙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這種話就講得不對了。至少在帝國主義消滅以前,報紙,各種意識形態的東西,都是要反映階級關系的。學校教育,文學藝術,都是意識形態,都是上層建筑,都是有階級性的。自然科學分兩個方面,就自然科學本身來說,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誰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學,是有階級性的。大學里,一個中文系,一個歷史系,唯心論最多。辦報紙的,唯心論最多。你們不要以為只是社會科學方面唯心論多,自然科學方面也有許多唯心論。搞自然科學的許多人,世界觀是唯心論的。你要說水是什么東西構成的,那他們是唯物論,水是兩種元素構成的,他們是照那個實際情形辦事的。你要講社會怎么改造,那他們是唯心論。我們說整風是要整好共產黨,他們中間一些人說要消滅共產黨。這一回暴露了這么一些情形。
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么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一點,就聽,話是一句不說。而且不通知團員,不通知黨員,也不通知支部書記,不通知支部委員會,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學校的黨委、總支里頭混進來一些敵人,清華大學黨委的委員里就有敵人。你這里一開會,他就告訴敵人了,這叫做“起義分子”。不是有起義將軍嗎?這是“起義文人”。這一件事,敵人和我們兩方面都高興。在敵人方面,看見共產黨員“起義”了,共產黨要“崩潰”了,他們很高興。這一回崩潰了多少呀?上海不曉得,北京學校的黨員大概是崩潰了百分之五,團員崩潰得多一點,也許百分之十,或者還多一點。這種崩潰,我說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總而言之,崩潰了我就高興得很。你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滿腦子唯心論,你鉆進共產黨、青年團里頭,名為共產主義,實際上是反共產主義,或者是動搖分子。所以,在我們方面,看見“起義”的,我們也高興。那一年清黨、清團清得這么干凈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們清理。但是,現在的情況變了,反過來了。我們把右派一包圍,許多跟右派有聯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來一揭露,他不“起義”了。現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義了。我三月在這里講話以后,一百天工夫,時局起了這樣大的變化。
這次反右派斗爭的性質,主要是政治斗爭。階級斗爭有各種形式,這次主要是政治斗爭,不是軍事斗爭,不是經濟斗爭。思想斗爭的成份有沒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爭占主要成份。思想斗爭主要還在下一階段,那要和風細雨。共產黨整風,青年團整風,是思想斗爭。要提高一步,真正學點馬克思主義。要真正互相幫助。有什么缺點,主觀主義有一點沒有呀?官僚主義有一點沒有呀?我們要真正用腦筋想一想,寫一點筆記,搞那么幾個月,把馬克思主義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擊右派也許還要幾十天,還要個把月。右派言論盡這樣在報紙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辦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論登的差不多了,也沒有那么多東西登嘛。以后就陰登一點,陽登一點,有就登一點,沒有就不登。我看七月還是反擊右派緊張的一個月。右派最喜歡急風暴雨,最不喜歡和風細雨。我們不是提倡和風細雨嗎?他們說,和風細雨,黃梅雨天天下,秧爛掉,就要鬧饑荒,不如急風暴雨。你們上海不是有那么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叫《烏“晝”啼》嗎?那個“烏鴉”他提此一議。他們還說,你們共產黨就不公道,你們從前整我們就是急風暴雨,現在你們整自己就和風細雨了。其實,我們從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評胡適、梁漱溟,我們黨內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風細雨的。世界上的事情總是曲折的。比如走路,總是這么彎彎曲曲走的。莫干山你們去過沒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盤。社會的運動總是采取螺旋形前進的。現在,右派還要挖,不能松勁,還是急風暴雨。因為他們來了個急風暴雨,這好象是我們報復他們。這個時候,右派才曉得和風細雨的好處。他看見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黃浦江里將要淹死的人一樣, 那怕是一根稻草, 他都想抓。我看,那個“烏鴉”現在是很歡迎和風細雨了。現在是暴雨天,過了七月,到了八月那個時候就可以和風細雨了,因為沒有多少東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員。我們中國歷來如此,有正面的教員,有反面的教員。人需要正反兩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第一個大好的反面教員。從前還有清政府,有袁世凱,有北洋軍閥,后頭有蔣介石,都是我們很好的反面教員。沒有他們,中國人民教育不過來,單是共產黨來當正面教員還不夠。現在也是一樣。我們有許多話他們不聽。所謂不聽,是什么人不聽呢?是許多中間人士不聽,特別是右派不聽。中間人士將信將疑。右派根本不聽,許多話我們都跟他們講了的,但是他們不聽,另外搞一套。比如我們主張“團結——批評——團結”,他們就不聽。我們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他們又不聽。我們講要民主集中制,要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又不聽。我們講要聯合社會主義各國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他們也不聽。總而言之,這些東西都講過的,他們都不聽。還有一條他們特別不聽的,就是說毒草要鋤掉。牛鬼蛇神讓它出來,然后展覽,展覽之后,大家說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讓它出來,然后鋤掉,鋤倒可以作肥料。這些話講過沒有呢?還不是講過嗎?毒草還是要出來。農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講,就是每年都要鋤它幾次,那個草根本不聽,它還要長。鋤了一萬年,草還要長,一萬萬年,還是要長。右派不怕鋤,因為我講話那個時候,不過是講要鋤草,并沒有動手鋤;而且他們認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花,我們這些人是毒草,他們并不是應當鋤掉的,而要把我們鋤掉。他們就沒有想到,他們正是那些應當鋤掉的東西。
現在就是辯論我上邊講過的那三個問題。社會主義革命來得急促,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沒有經過充分辯論,黨內沒有充分辯論,社會上也沒有充分辯論。象牛吃草一樣,先是呼嚕呼嚕吞下去,有個袋子裝起來,然后又回過頭來慢慢嚼。我們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層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識形態也好,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但是沒有展開充分辯論。這回經過報紙,經過座談會,經過大會,經過大字報,就是展開辯論。
大字報是個好東西,我看要傳下去。孔夫子的《論語》傳下來了,“五經”、“十三經”傳下來了,“二十四史”都傳下來了。這個大字報不傳下去呀?我看一定要傳下去。比如將來工廠里頭整風要不要大字報呀?我看用大字報好,越多越好。大字報是沒有階級性的,等于語言沒有階級性一樣。白話沒有階級性,我們這些人演說講白話,蔣介石也講白話。現在都不講文言了,不是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無產階級講白話,資產階級也講白話。無產階級可以用大字報,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大字報。我們相信,多數人是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的。因此,大字報這個工具有利于無產階級,不利于資產階級。一個時候,兩三個星期,天昏地黑,日月無光,好象是利于資產階級。我們講硬著頭皮頂住,也就是那兩三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你們不是講鍛煉嗎?有幾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這就是鍛煉,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爐里頭去燒。
有許多中間人士動搖一下,這也很好。動搖一下,他們得到了經驗。中間派的特點就是動搖,不然為什么叫中間派?這一頭是無產階級,那一頭是資產階級,還有許多中間派,兩頭小中間大。但是,中間派歸根結底是好人,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資產階級也想爭取他們作同盟軍,一個時候他們也有點象。因為中間派也批評我們,但他們是好心的批評。右派看見中間派批評我們,就來搗亂了。在你們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時,陸治,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個地方越亂越好,亂得越透越好。這是一條經驗。
剛才講大字報,這是個方式的問題,是取一種什么形式作戰的問題。大字報是作戰的武器之一,象步槍、短槍、機關槍這類輕武器。至于飛機、大炮,那大概是《文匯報》之類吧,還有《光明日報》,也還有一些別的報紙。有一個時期,共產黨的報紙也登右派言論。我們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論,要照原樣登出來。我們運用這種方式,以及其他各種方式,使廣大群眾從正反兩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報》、《文匯報》的工作人員,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們過去分不清什么叫無產階級報紙,什么叫資產階級報紙,什么叫社會主義報紙,什么叫資本主義報紙。一個時候,他們的右派領導人把報紙辦成資產階級報紙。這些右派領導人仇恨無產階級,仇恨社會主義。他們不是把學校引到無產階級方向,而是要引到資產階級方向。
資產階級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要不要改造?他們非常之怕改造,說改造就出那么一種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卑。這是一種錯誤的說法。應當是越改造越自尊,應當是自尊感,因為是自己覺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階級覺悟”很高,他們認為他們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無產階級。他們要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世界,而無產階級要按照無產階級的面貌來改造世界。我看,多數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經過躊躇、考慮、不大愿意、搖擺這么一些過程,總歸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覺得需要改造。共產黨還在改造,整風就是改造,將來還要整風。你說整了這次風就不整了?整了這次風就沒有官僚主義了?只要過兩三年,他都忘記了,那個官僚主義又來了。人就有那么一條,他容易忘記。所以,過一個時候就要整整風。共產黨還要整風,資產階級和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就不要整風?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風,更需要改造。
現在各民主黨派不是在整風嗎?整個社會要整一整風。把風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雞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線問題。現在民主黨派整風的重點是整路線問題,整資產階級右派的反革命路線。我看整得對。現在共產黨整風的重點不是整路線問題,是整作風問題。而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那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治、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么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要把我講的這三個問題搞清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幾億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要搞社會主義的話,要那一個黨來領導?是要章羅同盟領導,還是要共產黨來領導?來它一個大辯論,把路線問題搞清楚。
共產黨也有個路線問題,對于那些“起義分子”,共產黨、青年團里頭的右派,是個路線問題。教條主義現在不是個路線問題,因為它沒有形成。我們黨的歷史上有幾次教條主義路線問題,因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綱領。現在的教條主義沒有形成制度、政策、綱領,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東西,現在這么一錘子,火這樣燒一下,也軟了一點。各個機關、學校、工廠的領導人,不是在“下樓”嗎?他們不要那個國民黨作風和老爺習氣了,不做官當老爺了。合作社主任跟群眾一起耕田,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到車間里頭去,同工人一起勞動,官僚主義大為減少。這個風將來還要整。要出大字報,開座談會,把應當改正的,應當批評的問題都分類解決。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學一點馬克思主義。
我相信,我們中國人多數是好人,我們中華民族是個好民族。我們這個民族是很講道理的,很熱情的,很聰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于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現在要給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現在我們給右派穿。給右派一點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眾,要跟群眾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眾跟怕水一樣。你們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處提倡游水。水是個好東西。你只要每天學一小時,不間斷,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學會游水。第一不要請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個橡皮圈就學不會。“但是我這條命要緊呀,我不會呀!”你先在那個淺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說學一百天,你在那個淺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學會了。只要學會了,那末你到長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樣的,就是一種水,就是那么一個東西。有人說在游泳池淹下去還可以馬上把你提起來,死不了,在長江里頭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那里去找呀?拿這一條理由來嚇人。我說這是外行人講的話。我們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頭的教員、教授,原先不敢下長江,現在都敢了。你們黃浦江現在不是也有人游嗎?黃浦江、長江是一個錢不花的游泳池。打個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樣,各級領導者,就象游水的一樣,你不要離開水,你要順那個水,不要逆那個水。不要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呀!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學生群眾,民主黨派的多數成員,知識分子的多數,你不能罵他們,不能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水一樣不要脫離水。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象魚跟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
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后把尾巴變成個旗桿,那么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么呀?你們就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但是,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后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
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無產階級領導知識分子,還是知識分子領導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應當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沒有別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2],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就是吃五張皮的飯。第一張皮,是帝國主義所有制。第二張皮,是封建主義所有制。第三張皮,是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嗎?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第四張皮,是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第五張皮,是小生產所有制,就是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過去的知識分子是附在前三張皮上,或者附在后兩張皮上,附在這些皮上吃飯。現在這五張皮還有沒有?“皮之不存”了。帝國主義跑了,他們的產業都拿過來了。封建主義所有制消滅了,土地都歸農民,現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收歸國有了。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了,基本上(還沒有完全)變成社會主義的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了,盡管這個制度現在還不鞏固,還要幾年才能鞏固下來。這五張皮都沒有了,但是它還影響“毛”,影響這些資本家,影響這些知識分子。他們腦筋里頭老是記得那幾張皮,做夢也記得。從舊社會、舊軌道過來的人,總是留戀那種舊生活、舊習慣。所以,人的改造,時間就要更長些。
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干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這個地方講過,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現在沒有基礎了,他喪失了原來的社會經濟基礎,就是那五張皮沒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識分子現在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在空中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我說,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個梁上飛,他要回去,那邊空了,那幾張皮沒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沒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無產階級身上。你要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就要研究一下無產階級的思想,要跟無產階級有點感情,要跟工人、農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曉得那邊空了,但是還是想那個東西。我們現在就是勸他們覺悟過來。經過這一場大批判,我看他們多少會覺悟的。
那些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應當覺悟,尾巴不要翹得太高,你那個知識是有限的。我說,這種人是知識分子,又不是知識分子,叫半知識分子比較妥當。因為你的知識只有那么多,講起大道理來就犯錯誤。現在不去講那些右派知識分子,那是反動派。中間派知識分子犯的錯誤就是動搖,看不清楚方向,一個時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識,為什么犯錯誤呀?你那么厲害,尾巴翹得那么高,為什么動搖呀?墻上一克草,風吹兩邊倒。可見你知識不太多。在這個方面,知識多的是工人,是農民里頭的半無產階級。什么孫大雨那一套,他們一看就知道不對。你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大識字的人,他們知識高。決定大局,決定大方向,要請無產階級。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東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那里拿來的,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共中央好比是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錯誤。知識來源于群眾。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不要脫離群眾,我們跟群眾的關系,就象魚跟水的關系,游泳者跟水的關系一樣。
對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對這種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攻得他回頭。我們用各種方法切實攻,使他們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爭取他們,不說全部,總是可以爭取一些人變過來。他們是知識分子,有些是大知識分子,爭取過來是有用的。爭取過來,讓他們多少做一點事。而且這一回他們幫了大忙,當了反面教員,從反面教育了人民。我們并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里頭去,還是用治病救人這樣的態度。也許有一些人是不愿意過來的。象孫大雨這種人,如果他頑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們現在有許多事情要辦,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帶到棺材里頭去見閻王。你對閻王說,我是五張皮的維護者,我很有“骨氣”,共產黨、人民群眾斗爭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過來了。但是你曉得,現在的閻王也換了。這個閻王,第一是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寧。現在分兩個地獄,資本主義世界的閻王大概還是老的,社會主義世界就是這些人當閻王。我看頑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注釋
〔1)見《列子·天瑞》。
〔2)見《左傳·信公十四年》。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40-4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