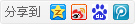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關于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我們業已在三篇文章(《無可奈何的供狀》⑴、《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中給了批評。這些批評,業已引起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他們并發表了許多正確的和有益的聲明、談話或評論。各種討論白皮書的座談會正在開,整個的討論還在發展。討論的范圍涉及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一百年來的中外關系,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系,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系,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斗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系中應取的態度,對于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這種現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的相互關系。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并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過去關于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區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側面充分暴露的緣故。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干涉。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偉大的勝利的中國革命,已經迫使美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一個方面,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干真實材料,并作出反動的結論,去答復另一個方面,另一個派別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公開暴露代替了遮藏掩蓋,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在幾星期以前,在白皮書發表以前,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盡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及其他幾個小帝國主義國家,至今還是如此。后起的,暴發的,神經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對,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對的美國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國主義系統,認為以公開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來和他們同伙中的對手辯論究竟哪一種反革命方法較為聰明的問題,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們企圖借此說服其對手,以便繼續他們自認為較為聰明的反革命方法。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了,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干(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他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么一回事。
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的信的開頭,提起他編纂白皮書的故事。他說他這本白皮書編得與眾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于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復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沒有刪略,盡管那里面有些話是批評我們政策的,盡管有些材料將來會成為批評的根據。我們政府對于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能夠感應,這便是我們的制度的固有力量。這種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正是右派和共產黨的極權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某些聯系是存在的。經過兩國人民的努力,這種聯系,將來可能發展到“極親密的友誼的”那種程度。但是,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系,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并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污,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系極不密切。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系”,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在這里,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系。對于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只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復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于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于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么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么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臺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對于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于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于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于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于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自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三國的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伙的幫手⑵。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于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于人民則是獨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斗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杰斐遜、林肯⑶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斗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遜一開口就錯了這許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是反動派。至于說,他的白皮書是怎樣一個“坦白記錄”這一點,我們認為坦白是有的,也是沒有的。艾奇遜們主觀上認為有利于他們一黨一派的東西,他們是有坦白的。反之,則是沒有的。裝作坦白,是為了作戰的目的。
注 釋
〔1〕 這是新華社編輯部寫的一篇評論,發表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
〔2〕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工人黨參加的情報局會議,作出《關于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對南共進行公開的指責,并把南共開除出情報局。當時,中國共產黨支持了這個決議。一九四九年情報局又通過《南斯拉夫共產黨在殺人犯和間諜掌握中》的決議。對這個決議中國共產黨沒有表示態度。關于對待南斯拉夫的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毛澤東在同南共聯盟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團談話時曾說: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一九四九年情報局罵你們是劊子手、希特勒分子,對那個決議我們沒有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采取這種方式,應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樣急。反過來,你們對我們有意見,也可以采取這種辦法,采取商量、說服的辦法。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黨,成功的例子很少。這次事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來說,是取得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
〔3〕華盛頓(一七三二——一七九九)、杰斐遜(一七四三——一八二六)、林肯(一八○九——一八六五),都是美國早期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華盛頓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一七七五——一七八三)的殖民地起義軍隊總司令,美國的第一任總統。杰斐遜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曾任美國總統。林肯主張廢除美國的黑奴制度,他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領導了反對美國南部各州奴隸主的戰爭(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并在一八六三年頒布了《解放黑奴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