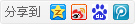媒體報道
毛澤東活用《三國演義》智慧指揮戰爭24年
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了2015年開年以來第一次政治局集體學習,學習的主題是“辯證唯物主義”。早在延安時期,黨內便開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大規模的學習。他們是怎麼學習的,又學些什麼呢?
毛澤東對哲學的研究,達到了如饑似渴的程度
毛澤東把歷史唯物主義視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確進行中國革命的重要工具,並感覺自己對此掌握得不夠,因此在長征到陝北後大力“做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馬列主義,而以哲學為主”。
他對哲學的研究,達到了如饑似渴的程度。親歷其境的美國記者斯諾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記》中描寫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時間專門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幾乎是什麼都不管了。”
1938年春,潘梓年出版了一本哲學著作《邏輯與邏輯學》,毛澤東對之感覺“頗為新鮮”,於是只用3天時間,就讀完了該書。
與此同時,他花費很大的精力研究哲學問題。據郭化若、莫文驊回憶,1938年9月間,毛澤東約集他倆和許光達、陳伯鈞、蕭勁光、蕭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十餘人,召開哲學座談會。“採取的方式是每週討論一次,晚上七八點鐘開始,持續到深夜十一二點鐘。每次討論都是由哲學家艾思奇、和培元等先講,然後討論。毛澤東除了插話,都是在最後講自己的看法。議論的中心圍繞軍事辯證法問題較多。實際上是對紅軍在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理論上的探討。”
毛澤東非常認真地探討有關問題,如對艾思奇《哲學與生活》中的“差別不是矛盾”的說法提出異議,致信說:“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對於陳伯達撰寫的《墨子哲學思想》,毛澤東寫信告訴他說:“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 用供參考”,並兩次詳列了他的七點意見和三點補充意見,致信張聞天“請轉伯達同志考慮……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
毛澤東經常會在重大會議上講矛盾觀,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資料中記錄,毛澤東說:“兒子轉化為父親,父親轉化為兒子,女子轉化為男子,男子轉化為女子,直接轉化是不行的,但是結婚後生男生女,還不是轉化嗎?”
“有紅白喜事……中國人結婚叫紅喜事,死人叫白喜事……中國人是很懂得辯證法的。結婚可以生小孩,母親生出小孩來,是喜事……新事物的發生,變化,死亡,百姓 們叫喜事。如果有人死了,會舉行一個追悼會。當人們為痛失親人而哭泣的時候,他們覺得,那也是一件喜事,實際上,確實如此。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兩千多歲了,就很妙。”——這是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第三次講話裏的部分內容。
每天上午九點以前為自學,每週集體討論一次
經過毛澤東的宣導和宣講,在延安形成了研究學習哲學的濃厚氣氛。
當時,成立了一些研究哲學的團體。頗負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學會,從1938年夏天成立,一直持續到延安整風運動後期,它集合了當時延安的哲學家和主要學者,舉辦各種哲學報告會、座談會和哲學年會。再如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會,毛澤東任會長,陳雲任副會長,參加者有黨政軍主要負責幹部四五十人,它也堅持到1942 年,主要學習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1940年,先後成立了“自然辯證法討論會”和“自然科學研究會”。到1941年底,該研究會會員達330人。
團體之外,還有許多學習小組。如毛澤東組織的哲學小組,參加者有艾思奇、陳伯達、吳黎平、葉子龍等。每週活動一次。每次總是毛澤東先提出一些問題,讓大家準備,然後一起討論。
楊超回憶說:“當時毛主席在小組中徵求對他著作的意見,討論時毫無拘束,就在他家中開會……我們在討論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階段的論述,在會議中大家都敞開思想,發言踴躍。對主要矛盾階段問題討論中有人講:‘主席,如果說有主要矛盾階段,那麼非主要矛盾階段和次要矛盾階段如何解釋?’以後,主席就把 這種思想概括在《矛盾論》中矛盾運動的形式、過程、階段的概念中,充實了矛盾運動過程論的思想。”
張聞天在中央宣傳部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後來中央文委、中央辦公廳等機關的人員也都來參加,學習小組擴大成為一百多人的學習集體。“這個小組是依照艾思奇同志的提綱進行學習的。提綱是分章分節寫的。艾思奇同志每一個星期或兩個星期寫一節。寫完一節,就油印出來,發給全組的同志。”中央組織部也成立了一個學習小組,陳雲與李富春任正副組長。他們每天上午九點以前為自學,每週集體討論一次。學習小組重點學習哲學,將《唯物史觀》作為教材。
此外,還經常舉辦各種類型的哲學演講。當時在延安的學者和培元、艾思奇、吳亮平、柯柏年、王學文、王思華等都有大量的哲學演講,他們有的講軍事辯證法,有的講實際生活中的哲學問題,有的介紹中外 哲學史方面的知識,有的介紹哲學方法。其後,這些演講大都發表在延安當時出版的《解放》週刊、《中國文化》月刊、《八路軍軍政雜誌》和《解放日報》上。
學習特別用功,都是那段時間學哲學養成的習慣
前所未有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學習熱潮,當然也對黨的理論建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當時,研習哲學成為全黨的風尚。由於明確了哲學的重要性,所以哲學被列入延安在職幹部教育計畫,廣大幹部也積極參加到學習哲學之中去。
身經其事的鄭校先回憶說:“1939年底我入軍政學院學習,除集中上課外,其他時間主要就是閱讀學院發的教材,自學時間較多。馬克思、恩格斯原著《資本論》 《費爾巴哈論》《反杜林論》等書,很難讀懂,要逐字逐句很費力地去研讀、去理解,每小時只能讀5頁左右,等於是硬啃下來的。”
不僅在延安,敵後抗日根據地也是一樣。1940年朱德在延安召開的學習大會上指出:我們是跟著延安走的,這裏學什麼,我們那裏也學什麼。教育學習,在抗日前線,辯證法大大地發展了;現在許多幹部都能把哲學上的原則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了。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學習中,認識客觀實際、遵循規律成為許多領導人的共識。葉劍英就指出:世界上一切東西的發展都有它的規律性,獲得這個規律要具有一個武器, 這就是唯物辯證法。要把唯物辯證法正確地運用在軍事領域中,作為判斷情況、下定決心、指導戰爭的法寶。在一定意義上,大規模的哲學學習為延安整風運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此外,很多黨員的理論水準和工作能力也在這種學習中大幅提高。陳雲的話很有代表性,他後來多次講到:在延安那段學習對他幫助很大,自從學習哲學以後,講話做事才有了唯物論、辯證法,可以說終身受用。李先念也是運用哲學武裝自己的一個典型。1938年他入馬列學院學習,“學習特別用功”,他說都是那段時間學哲學養成的習慣。
在《三國演義》裏讀到辯證法
在很多人看來,毛澤東的一部分辯證思維來自 於《三國演義》。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永新縣境內三灣村,在這裏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那天深夜,毛澤東來到借住的三灣村“協盛和”雜貨店,他將床鋪搭在簡陋的櫃檯上,正準備躺下睡覺時,順著微弱的燈光,偶然瞥見貨架櫃頂上放著一摞落滿灰塵的書。愛看書的嗜好,使他將之取了下來。原來這是一套線裝本的《三國演義》。頓時,毛澤東眼睛一亮,睡意全無。第二天一早便向店主借閱。就這樣,這套《三國演義》伴隨著他度過了在三灣的晝夜。
1938年10月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還對賀龍和徐海東兩位將領開玩笑說:“中國有三部小說,《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誰不看完這三部小說,誰就不算中國人。”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對《三國演義》是多麼的喜愛。
毛澤東在著書立說、報告演講、漫談閒聊中,對《三國演義》爛熟於心,用起來幾乎到了張口即出、信手拈來的程度。
在《三國演義》“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話中,毛澤東看到了“符合辯證法”的合理內核;在周瑜和諸葛亮引用的“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的俗諺中,毛澤東讀出了“自然辯證法”,用以解釋生與死、禍與福、憂患與安樂、必然與偶然的統一;在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和彝陵之戰“三大戰役”中,毛澤東讀出了“軍事辯證法”,正確揭示了優勢與劣勢、強大與弱小、驕兵與哀兵、進攻與防禦、先發制人與後發制於人、客觀條件與主觀條件、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 的辯證法。
《三國演義》是一部活的兵法,是一部形象的戰爭史。毛澤東說,《三國演義》是他讀過的“第一本軍事教科書”。毛澤東指揮戰爭長 達24年,“三國智慧”時常縈繞於毛澤東的腦海裏,可說無役不與。他把《三國演義》用活了。許多戰例,其虛實分合,攻守進退,以小打大,以少勝多,應戰應和,應擒應縱,勝負得失,都有可鑒之處。這也可以解釋為毛澤東把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用活了。